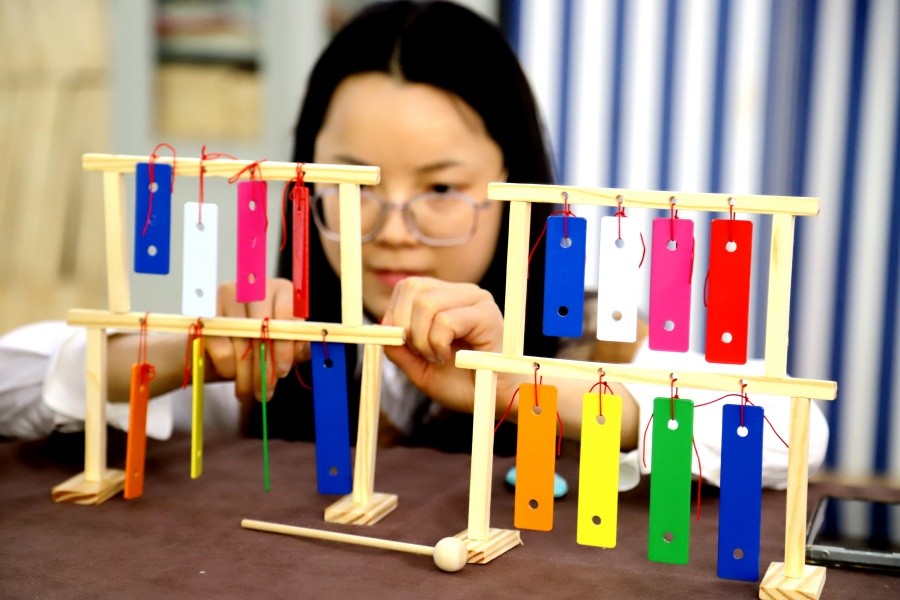安徽省重點新聞門戶網站
安徽省重點新聞門戶網站
 安徽青年報官方網站
安徽青年報官方網站
“拾荒主席”張景蘭:做一個人的女兒 一群人的媽媽
"我不是媽媽,我是王小鳥啊。"5月9日,在合肥市第三人民醫院的病房里,77歲的張景蘭一遍一遍的對母親王文珍說。已經102歲的王文珍糊涂起來時,就會把女兒叫做媽媽,每當這時張景蘭就會不厭其煩念著這句話安撫她。
"她是全世界最好的媽媽,我覺得我對不起她。"在母親節來臨之際,張景蘭看著臥床的母親落下眼淚。"她跟我一起撿破爛資助貧困孩子十八年,也是因為跟我一起撿破爛,她才摔倒住院的。"
從工會主席到拾荒老人, 她收廢品助力新生
1948年在淮南出生的張景蘭有著截然不同的雙重身份,在2008年退休前,她擔任安徽省人大機關工會主席,退休后則成了一名拾荒者。但從1998年起,二十多年來,不變的是她對貧困兒童的資助。
1997年的一次對口幫扶活動,讓張景蘭去到績溪,聽到了這樣一段話。"他們說績溪有三個傳統,給小孩念書,給活人蓋房,給死人修墓,但是所謂的給小孩念書,有錢人家是男女都念,沒錢人家就只有男孩上學。"作為農村出身、半工半讀學完電大的女性,張景蘭當即決定要資助女童,還要號召大家一起做。10年間,在張景蘭的奔走號召下,從女童到各類殘疾、貧困學童,安徽省人大機關共資助了200余名困難學童。
退休后,張景蘭雖然有穩定的退休工資,但要一個人贍養母親,還要還因為購房欠友人的房款,她的手頭并不寬裕,為了繼續對孩子們的資助,她開始拾荒攢錢,每年資助30名困難學生每人500元。
在張景蘭家里,記者幾乎沒看到什么家電,唯一在運行的冰箱還是別人送的,家具也不多,把房間填滿的是張景蘭收回后還沒來得及賣出的廢品,因為母親住院后,母女倆很長時間不回家住了,連床上都變成了廢品的暫居地。
陪著母親住院的張景蘭偶爾還是會在晚上去撿些塑料瓶和紙殼,再由志愿者幫她運回家或者賣掉。收廢品的十余年間,"百腦匯"是張景蘭常去的拾荒點,里面的不少商家都了解了她的故事,主動把廢品留給她,有的成為了經常照顧她的志愿者。
"老媽媽"與"老姑娘",拾荒點亮學子希望
張景蘭幼年喪父,與母親相依為命多年,直到從淮南調到合肥工作才與母親兩地分隔。每到除夕夜,萬家燈火亮起,一朵朵煙花綻放在團圓之夜,張景蘭眼里看到的是一個6~8角錢的煙花殼子,為了除夕夜的這一筆"大買賣",張景蘭十幾年都沒回家過年,直至2017年把母親接到合肥。
"媽媽有一次說,別人都在放炮仗,我的孩子在那拾破爛,我聽到后就止不住的想哭。"張景蘭說,她給母親寄回家的錢,母親也不花,還在老家撿破爛,收舊衣服給她,支持她資助貧困學子。
"每次我回家,媽媽總會講孩子你要吃什么,我給你買,我給你燒。"那時張景蘭的母親已經八十多歲,她自己在家把收來的舊衣服一件件開水消毒、搓洗干凈,給張景蘭送給貧困的孩子,洗的雙手指尖生疼。
"我媽的品格非常好,她是我的第一老師。"張景蘭回憶,小時候她去別人家里拜年,母親不允許她拿別人家一塊糖,母親這些點滴的教導,塑造了張景蘭堅強又無私的性格。
"我們老家離火車站一站多路,我們舍不得坐車,我媽媽就陪我一道,帶著她洗好的舊衣服、舊鞋子,推著一個車走過去,下午一點的車,我們早上八點就出發,那時候車站對我們都有印象,一個老媽媽送一個老姑娘。"張景蘭回憶著和母親的經歷,忍不住落下眼淚。
2018年,原本還能跟著張景蘭走街串巷收廢品的王文珍因為摔了一跤沒能再離開病榻,張景蘭因此也自責萬分。"那天下了雨,我把廢品先收在一個地方,讓媽媽在那等我,我先送去賣一趟,結果回來時我遠遠的開始叫她,沒聽到回聲,趕回去一看,她踩到坑里摔倒了。"
王文珍的長期住院讓張景蘭的經濟狀況更加不樂觀,2024年,她不得不從每年資助30名貧困學子,變為資助10名學子,但是她依舊不愿意停下。
資助服刑人員子女 ,她是一群人的媽媽
5月11日是母親節,張景蘭受邀到青山監獄與服刑人員分享故事,因為她還在資助著家庭困難的監獄服刑人員子女。
最初她是受邀到蜀山監獄為服刑人員進行演講,用自身的故事促進他們的思想轉變,但在這個過程中,她了解到有服刑人員的子女因為家庭困難影響學業,"他們犯了法,但是子女是無辜的",張景蘭"拾荒"的擔子上,又挑起了這些孩子的希望。
"有一位服刑人員哭著跟我說,他收到了孩子的來信,孩子說考了第二名,他沒想到自己犯了罪,自己的孩子還能受到資助。"張景蘭說,還有的服刑人員受她事跡的影響,也拿出自己在獄中做工攢下的錢,想要資助孩子。
張景蘭幫助了數十位服刑人員的子女,她的事跡更是感染著他們,在蜀山監獄里,大家把張景蘭叫做張媽媽。
"我為什么要資助這些學生,第一,我虛歲三歲時父親去世,除了媽媽千辛萬苦的照顧,是黨和人民培養我長大,第二,青少年是國家的希望,要叫他們做德智體美勞的好學生,第三,我是中共黨員,應該努力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張景蘭說,因為這三點,她有用不完的勁,再困難,也會把資助貧困學子堅持下去。
大皖新聞記者 于源綺/文 見習記者王騰飛/圖
責任編輯:祁夢寶
- 2025-05-14 古井園保護區赴主簿鎮南田村調研
- 2025-05-14 預防欺凌 向陽而生——阜陽市第二十九中學舉辦法治報告會
- 2025-05-14 合肥市螺崗小學:傳承革命精神 探索科教奧秘
- 2025-05-14 渦陽第一中學:皮影承非遺 薪火映青春
- 2025-05-14 【學霸養成記】岳漢:思維與生活同頻共振



 贊一個
贊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