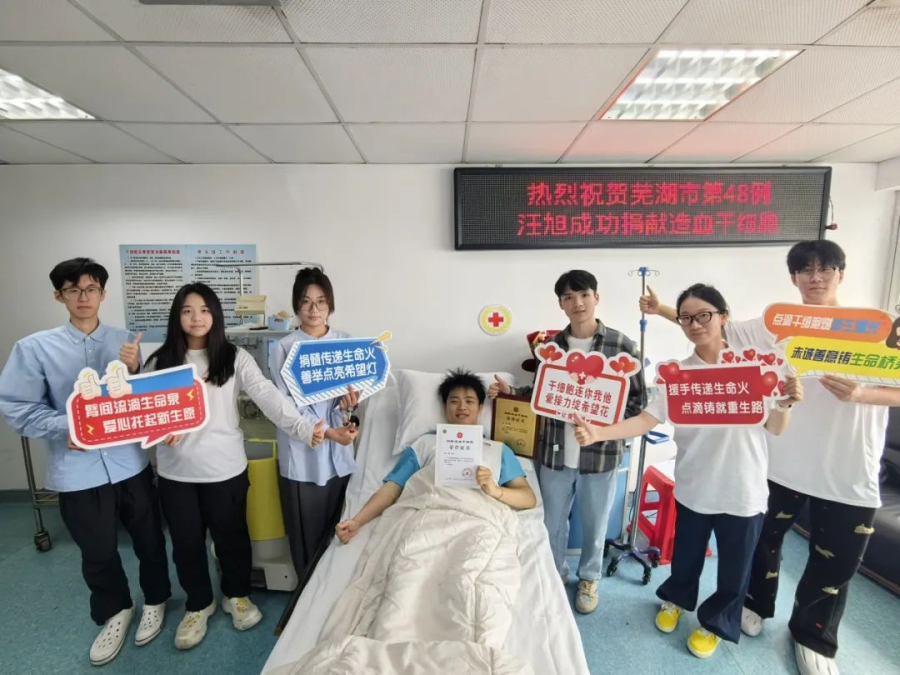安徽省重點新聞門戶網站
安徽省重點新聞門戶網站
 安徽青年報官方網站
安徽青年報官方網站
【文化中國行】這股山野的風,吹得有多“勁”
望江縣長嶺鎮黃梅戲協會表演的黃梅戲《羅帕記》選段。(資料圖片)視覺安徽
日前,懷寧縣黃梅戲愛好者都飛飛在給孩子們做示范。 本報通訊員 趙赟 攝/視覺安徽
近日,民間黃梅戲愛好者在桐城六尺巷景區五畝園內表演。本報記者 陳成 攝/視覺安徽
被譽為“中國鄉村音樂”的黃梅戲,生于鄉野、沾雨帶露,天然帶著濃郁的鄉土氣息。田間地頭的民間劇團,堅守戲曲誕生的土壤,堅持在戲迷身邊演出,守住戲曲生命線。
在安慶,400多家民營戲劇團與民間班社扎根鄉野,4000余名從業人員堅守舞臺,還有數以萬計的戲迷票友熱情參與。《安慶市黃梅戲保護傳承條例》實施三年來,用法治護航接地氣的演出生態,讓戲韻新聲在人們身邊回響,讓帶著泥土芬芳的戲曲力量強勁生長。
從“草臺班子”到“專業范兒”——
在堅守與變革中蝶變
7月1日下午1點,六安市舒城縣萬佛湖鎮長崗村村民廣場上,一輛拉著“送戲進萬村”橫幅的白色舞臺車穩穩停駐。字幕顯示屏、音響準備就緒,化妝間內不時傳來咿呀的吊嗓聲......一出好戲即將上演。
“這是今年在舒城的第28場演出,基本上場場爆滿。”望江縣百花文化傳媒演藝有限公司總經理王建華站在后臺,望著逐漸聚攏的村民,眼神中滿是欣慰。
“村民愛看,我們愛演,這就是我一直堅守在戲曲行當的原因。”王建華說。
然而,這份堅守背后,是數不清的艱辛。今年59歲的王建華,出生在有“中國民間文化藝術之鄉”美譽的望江縣高士鎮。兒時,父母哼唱的黃梅調就是他的搖籃曲。
20多年前,懷揣著對黃梅戲的熱愛,他在高士鎮創辦百花黃梅戲劇團。那時,兩只戲箱、簡單道具和十幾套戲服就是劇團全部家當。
最苦的是“找飯吃”。沒有政策扶持,劇團十幾個人挑著箱子翻山越嶺,逢人就問“要唱戲嗎?”“最遠走過二十公里山路,晚上沒地方睡,就在祠堂打地鋪;戲服破了,補丁摞補丁;燈沒油了,就摸黑對詞。”回憶過往,王建華感慨萬分。演出條件雖簡陋,可是只要鑼鼓一響,孩子們就扒著舞臺沿兒不肯走,老人們笑呵呵地說“比電視里聽得真切”。
就為這股熱乎勁兒,王建華咬著牙撐了下去。
轉機出現在2014年前后。“省里啟動‘送戲進萬村’項目,民營院團也能投標。”王建華至今記得拿到第一份政府購買合同時的激動:每場演出費4400元,除去成本凈賺近2000元,劇團不再四處“化緣”了。
不久后,王建華把劇團升級為公司,注冊資金120萬元。如今,舞臺車取代了沉重的挑擔,LED燈光將舞臺照得通亮,演員的戲服每年更新。更讓王建華欣慰的是,收入穩定后,劇團能留住人了。現在劇團的40余名演員中,既有戲曲科班畢業生,也有經驗豐富的二級、三級演員,專業人才梯隊逐步成型。
下午兩點半,大幕準時拉開。熟悉的黃梅戲旋律響起,臺下立刻爆發出熱烈的喝彩聲。“硬件條件變了,但戲魂始終沒變,觀眾的喜愛也一直都在。”王建華說。
如今,百花演藝公司每年除承接400余場“送戲進萬村”演出外,還有大量商業演出,足跡遍布安徽、江西、湖北等地,年收入超300萬元。該院團還獲評為安徽省“百佳院團”。
從田間地頭的草臺班子,到專業規范的演藝公司;從四處奔波的艱辛,到廣受贊譽的榮光,百花劇團的蝶變之路,也是安慶民間劇團發展的縮影。正是這些扎根基層的戲曲力量,將黃梅戲的種子播撒在千家萬戶,讓傳統藝術在新時代煥發勃勃生機。
從“老腔老調”到“新曲新韻”——
在傳承與創新中前行
相比專業院團,民間院團的特色在哪?采訪中,不少受訪者給出了答案:更接地氣,靈活性更高。民間劇團規模小、人員精簡,劇目編排與場地選擇十分靈活,能迅速響應市場需求,而且演員大多來自民間,表演中融入方言民俗,容易引發觀眾共鳴。
以宿松縣群芳演藝有限公司為例,作為當地最“老”的民營劇團之一,其戲箱里不僅“裝”著《天仙配》《女駙馬》等經典黃梅戲,還有文南詞這門被稱為“黃梅戲姊妹篇”的地方小調。
文南詞作為“戲曲活化石”,在宿松這片土地上扎根生長已近300年。農閑時搭起草臺,藝人懷抱漁鼓、拉響四胡琴,就能吸引十里八鄉的鄉親搬著竹椅前來觀賞。
但前些年,群芳演藝公司負責人汪方榮犯了愁:年輕人覺得文南詞“土氣”,老戲迷又認為其失去了傳統韻味。
觀眾喜歡啥?汪方榮帶著劇團成員一頭扎進村里,跟大爺大媽們嘮嗑,同年輕人閑聊,又多次請教文南詞老藝人。幾番打磨后,聚焦孝文化的《關我什么事》驚艷亮相,故事唱進了百姓心坎。
“現在,《關我什么事》已成為劇團的看家劇目。”汪方榮笑著說。
這樣的創新案例在安慶民營劇團中并不鮮見。懷寧縣洪鋪鎮的金義黃梅戲劇社新編的黃梅戲《碧血贊歌》,聚焦紅色故事,讓人動容;望江縣長嶺鎮的雷陽花劇團新編的黃梅戲《陳旺脫貧》聚焦鄉村振興主題,鼓舞人心......
一個戲曲劇種的生生不息,離不開新人輩出與觀眾迭代。在安慶,一批批滿懷熱忱的黃梅戲愛好者自發投身到育人事業,或是開辦公益培訓班,或是到學校授課,為黃梅戲傳承而努力。
年過七旬的時小柳、都飛飛夫婦是懷寧縣的黃梅戲愛好者。二人長期開展公益教學,足跡遍布懷寧縣各個中小學及各類活動現場,編排黃梅戲創新融合節目超百個,帶教過的學生超百人,多人在戲曲大賽中斬獲佳績。
在太湖縣徐橋鎮老年大學,黃梅戲是搶手課。課上,學員們認真聆聽發聲技巧,不時跟唱練習。課后,這些“銀發學員”還自發加入戲迷協會,活躍在鄉村文化大舞臺。
“年輕時就愛聽黃梅戲,現在能跟著專業老師學,圓了我的夢。”今年56歲的袁協霞說。
從“田間地頭”到“時代舞臺”——
在融合與傳播中升華
夜色降臨,桐城市六尺巷景區的五畝園內,婉轉的黃梅戲唱腔悠然響起。
“正哪月十呀五......”在古色古香的園林戲臺上,《夫妻觀燈》《對花》等經典選段輪番上演。
自今年5月開園以來,五畝園運營方便與民間黃梅戲藝人攜手,將園林景致與戲曲藝術巧妙融合,打造沉浸式演出體驗。游客漫步其中,既能欣賞江南園林的詩意,又能感受黃梅戲的獨特韻味。
“在這里演出,不僅有了穩定收入,更重要的是能讓很多外地游客近距離接觸黃梅戲,愛上這門傳統藝術。”黃梅戲演員王亞麗說。
黃梅戲宛如鄉野間拂來的清風,而民間黃梅戲劇團和黃梅戲愛好者們正是這縷清風的有力推動者。如今,這股戲曲之風,不僅從田間地頭吹向繁華景區,更跨越千山萬水,飄向祖國各地。
去年12月,金義黃梅戲劇社社長胡節銀便帶隊奔赴新疆,與當地演員們共同排練黃梅戲《女駙馬》。“當地籌備大型晚會需排演黃梅戲節目,而本地演員對黃梅戲陌生,通過網絡了解到我們劇社,這才邀請我們過來指導。”胡節銀告訴記者,節目演出后,大獲好評,他今年又收到不少來自新疆的邀約。
這場跨越千里的藝術交流,讓黃梅戲的藝術種子就此在邊疆扎根發芽,也讓民族團結之花在皖疆兩地群眾心中絢麗綻放。
從鄉土中汲取養分,在創新中突破自我,在政策的支持下茁壯成長,安慶民間黃梅戲劇團正以昂揚的姿態,書寫著黃梅戲傳承與發展的新篇章,它們的“拔節生長”,不僅是一個個劇團的發展歷程,更是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煥發新生的生動寫照。
■ 本報記者 陳成
責任編輯:李志慧

- 2025-07-03 今日辟謠(2025年7月3日)
- 2025-07-03 宛新平:馬鞍山車站“聽勸”背后的“民呼我應”



 贊一個
贊一個